
新編上古音三十部諧聲表.apkg
227.7KB
|
 哲豪 更新日期:2022-04-12 17:10:27
哲豪 更新日期:2022-04-12 17:10:27以下為書中註釋,本人根據王力先生的諧聲表,融入書中註釋內容,生僻部分增加注音,統一編排,力求方便記憶,歡迎採用記憶。
另外,由於本人系音韻學初學者,難免有錯誤之處,請各位同學批評指正。
現在,隨著地下出土文獻資料的增加,文史學界進行古代典籍文獻及古文字學的研究者也在逐漸增多。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文字、音韻、訓詁等古人所謂的“小學”知識就成為研究者必需學習的內容。其中的音韻學向來被視為“絕學”,要想達到熟悉的程度尤其困難。不過,作為入門,熟記上古音諧聲表可以說是一個必要的步驟。清人段玉裁說:“於十七部(段氏將古音分為十七部)不熟者,其小學必不到家,求諸形聲,難為功也。”(劉盼遂編《段玉裁先生年譜》,《經韻樓集·附》,45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為方便初學者掌握要領,段玉裁編有《古十七部諧聲表》(《說文解字注·附<六書音均表>二》,818-829頁,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後又委其弟子江沅撰《說文解字音均表》二卷(《續修四庫全書》第247冊,197-22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楊樹達在《說文古韻二十八部聲系序》中曾說:“比年以來,余研治聲訓,勘校《說文》,於江子蘭(即江沅)之《十七部均表》未嘗一日去手。”(《積微居小學述林全編》,44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繼段玉裁、江沅之後,清人江有誥編撰《廿一部諧聲表》一卷(《續修四庫全書》第248冊,239-25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在諧聲偏旁的擇取上較段氏所編更為合理。隨著古韻分部日趨細密,作諧聲表者代不乏人。民國時期,在黃侃分古韻為二十八部的基礎上,權少文編撰《說文古均二十八部聲系》(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曾經錢玄同、沈兼士、楊樹達、王力、聞一多諸先生審訂,楊樹達、王力、黎錦熙為之作序,由此可見當時學者對諧聲表編撰工作之重視。如今的高校文史教學中,基本上都是採取王力先生分先秦古韻為三十部的觀點。王力先生編有“諧聲表”,以諧聲偏旁見於《詩經》者為准(王力《漢語音韻》,173-186頁,中華書局,2003),雖說重點突出,便於記誦,然未免有些簡略。其弟子如陳復華、何九盈也都編有“諧聲表”(陳復華《漢語音韻學基礎》修訂本,157-168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何九盈《上古音》,29-59頁,商務印書館,1991),較王力先生僅取諧聲偏旁見於《詩經》者更為全面,因而也更具合理性。馮蒸先生在《漢語音韻學應記誦基礎內容總覽(續二)》中(《漢字文化》2005年第1期,24-26頁)基本採取王力先生所作的“諧聲表”,過於簡略的局限是很明顯的。同時,王力先生原表中有某些顯然是排版錯誤之處,如“鐸部”中的“”顯然是“炙”之誤,此表亦沿襲,實屬不當。而且,隨著古文字學研究的深入,學術界對某些諧聲偏旁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王力先生原表中某些諧聲偏旁的分析也有據新出成果加以進一步說明的必要。在繼承諸位前輩學者的工作尤其是王力先生所做“諧聲表”的基礎上,同時吸收古文字學界對字形分析的最新研究成果,我們重新編寫了“上古音三十部諧聲表”。此“諧聲表”主體部分沿襲王力先生原有的內容,對於王先生的原有注釋有需要進一步說明之處用“侯注”予以標示,同時補充其他見於《說文》的諧聲偏旁,力求做到全面準確。重新編撰此表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方便讀者記誦,故對某些不常見的諧聲偏旁及文字標注漢語拼音兼及釋義,以免卻讀者翻檢查詢之勞。諧聲偏旁的歸部有歧說者,大多採取最為通行的說法,以免繳繞。為避免某些繁體字與簡體字字形重複,如“後”的簡化字與“后”重複,諧聲表的內容及注釋一律採用繁體字。
版权声明:【资源网】平台全部资源均由用户制作发布,平台无在线支付业务,无任何盈利行为,用户上传时已签《版权责任承诺书》自行承担版权责任,若此资源侵犯了知识产权且您是版权方请发送反馈信件至ankichinas@163.com联系平台,感谢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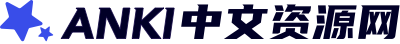
 学习使朕快乐
学习使朕快乐
 用心好学
用心好学
 子坎法硕
子坎法硕